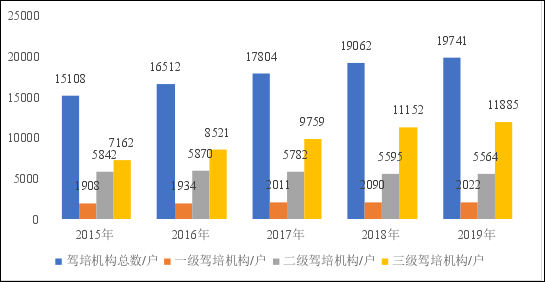正午书架 |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在《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中,莫蒂默以时间线索为主轴,以“变化”为主题,梳理分析了欧洲自11世纪到20世纪,在社会基本面貌、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所发生的最重大、最关键“变化”,带领读者开展了一趟关于探险、发明、革命与剧变的千年旅程。标题为编者所拟。
2019年08月02日伊恩·莫蒂默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正午
编者按:《欧罗巴一千年》全书以时间线索为主轴,从11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细数每一百年里欧洲发生的最重大变化,给出了过去这一千年里最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十个人、五十件大事。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文| 伊恩·莫蒂默
译| 李荣庆 刘富丽 缪羽龙 赵学峰 陈逢丹
印刷、火器、方言、时间计量、知识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城市化……哪个是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大影响的改变?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彼得•阿伯拉尔、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哥伦布、马丁•路德、伽利略、马克思……谁是改变世界最大的人?为了安全便利的生活、为了追求财富,人类不断打破神圣、地理、等级、语言、时间等概念的边界。11-20世纪的欧洲,见证了这些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生活。然而,石化燃料即将告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劣,人类,还能继续前行吗?
近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博士伊恩·莫蒂默的著作《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在书中,莫蒂默以时间线索为主轴,以“变化”为主题,梳理分析了欧洲自11世纪到20世纪,在社会基本面貌、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所发生的最重大、最关键的“变化”。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终于在某些阶段跨过了一些门槛、进入了新的高度,而这些飞跃则持续影响整个人类和人性。
伊恩·莫蒂默认为,20世纪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个重大变化是:全球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以及我们生活水平的不可持续性。
伊恩·莫蒂默坚信,“若人类再能存在1000年,我在本书中选取的那些最深刻的变化会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始契机”。
我们节选了书中第四章《 14世纪:黑死病·射击战·民族主义·方言》中“黑死病”的部分。

当地时间2015年3月10日,法国巴黎,考古学家在墓地工作。考古工作者与建筑工人一起掘开法国巴黎市中心的一家“不二价”超市的底部时,发现令人震惊的一幕,200余具人类尸骨排列整齐地被埋藏在地下,专家推测他们死于中世纪的黑死病。来自视觉中国
1301—1400 14世纪:黑死病
中世纪的人们不懂社会史。当艺术家将《圣经》或古代罗马故事描绘于彩色玻璃上、再现于雕塑上以及插画手稿中时,他们展示了人们身着中世纪服饰、居住于中世纪的房屋、操控中世纪的船只的情景。但试设想一个极其博学又富有想象力的修道士,1300年在他的修道院里翻阅他能利用的一切史料,这无疑会让他相信人类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很幸运。或者用他那个时代的宗教话语来说:上帝对基督教世界一直很眷顾。经济上,西欧越来越强大,人口越来越兴旺。曾胆战心惊害怕受到攻击的城镇居民,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保护,乡村地区也不再受到威胁。这位修士可能理所当然地把教堂视为这些发展的主要建设者和推动者。在推动基督教世界的向外扩张上,在安抚内部派别纷争上,在将武力锁定在边远的特定目标上,教会扮演着和平使者的角色。教会帮助许多人学会了读书写字。它为基督徒制定了道德守则,鼓励法庭对破坏道德准则者实施惩罚。我们这位假想的修士可能很自信:上帝正在倾尽全力为整个基督教世界谋福祉。不过100年后他可能就不会如此自信了。
到1300年,形势已经开始不断变化。在13世纪最后的十年里,粮食连年歉收导致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食物严重短缺。1309年,雨水过多引起整个欧洲的大饥荒。接着,情况越来越糟。当然过去也有很多荒年,但灾后的粮食丰产,总能使人口迅速反弹。可是这回情况就不一样了。几十年的过度种植使土壤的含氮量持续减少,仅仅靠休耕已不再能够恢复土地的肥力了。1200年小麦产量曾高达6∶1(每播下一粒麦种,可以有6粒麦子的收获),到了1300年,小麦的产出和投入则只有2∶1了;而大麦和黑麦产投比则从4∶1减到了2∶1。土地生产率如此低下,人口的快速恢复已是不可能的了。假设一个农民拥有25 英亩的耕地,这对于一个14 世纪早期英国的庄园佃户来说面积够大的了。又假设前一年是个丰年,他有了足够的玉米种子。他播种了50蒲式耳(约等于1820升——编者注)的玉米,并达到5∶1 的产投比,因此他从25英亩土地上可以收获250蒲式耳玉米。那年年底,假使他相信来年还会有5∶1 的产投比,他可能会这样分配他收获的玉米:留出50蒲式耳玉米做种子,50蒲式耳玉米留给牲畜,75蒲式耳留给自己和家人,还剩75蒲式耳则拿到市场出售。但是,假如来年是个凶年,只有3∶1 的产投比,他就只能收获150蒲式耳玉米了。如此一来,他就拿不出什么到市场贩卖了。除了家庭和牲畜用粮,他只剩下25蒲式耳玉米种子,这是他播种所需种子的一半。即使第三个年头又有5∶1 的产投比,他也只够养活家庭和牲畜,没有多余的玉米留做种子了。
实际的情况比上面的例子还要艰难得多。多数农民都没有25英亩地,粮食产投比降至3∶1,而且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三年一次的歉收。霜降过早或过晚都能导致颗粒绝收,此时平均气温骤然下降,在高地地区引起严重后果,数以千计的人们死于饥饿。当粮食连年歉收时,灾难就势所难免。因此,欧洲人口甚至在1315—1319 年那几场可怕饥荒之前就开始下降。据估计,曾有10%的人口死于这些自然灾害,这意味着基督教世界有超过1000 万人要么饿死,要么死于营养不良。它标志着三个世纪以来几乎不间断的人口和商业增长的结束。
但对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简直算不了什么。
很难真正传达出黑死病的毁灭性质。每当我做关于14世纪英格兰的报告,强调1348—1349年是多么悲惨时,总会有人坚称它不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或不像闪电战一样令人恐惧。我解释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年内英国的死亡率占总人口的1.55%:平均死亡率为每年0.4%。而当黑死病像波浪一样在全国传播时,大约七个月的时间里,就有约45%的英国人因此死亡:年死亡率为77%。因而,1348—1349年的死亡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0倍。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拿黑死病跟“二战”的轰炸比较:如果要复制瘟疫造成的死亡,我们除了在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每颗原子弹造成7万或0.1%的人口死亡),还要扔450颗这样的炸弹。也就是说七个月里每天在不同的城市里都有两颗原子弹发生爆炸。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没人会怀疑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是那场瘟疫发生的时间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跟那些受害者的文化又如此生分,因而无法体会如此大规模死亡的感受。我们发现与14世纪里整个社区被消灭殆尽的命运相比,我们更容易理解“一战”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伤痛。
黑死病是第二次由动物疾病引起的流行病的第一波爆发,由于受染者的腹股沟和腋窝发生黑色淋巴结炎,通常也称为淋巴腺鼠疫。其病原体是一种杆菌,或称鼠疫耶尔森菌,通常由寄生在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携带,但也可以被人蚤传播。在某些情况下,它也能通过感染者的呼吸传播。当今的看法是,如果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肺炎,人就会呼出病菌,而疾病就会通过空气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这种形式下,把黑死病描述成淋巴腺鼠疫就不对了,它是一种危险性更大的肺炎鼠疫。
第一次大流行病发生在公元541年。那次黑死病的“先驱”在整个6世纪都持续毒害着人们,但威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弱。最终于8 世纪60年代消失。到1347年为止,这600 年间欧洲几乎没有瘟疫,因此再次出现的后果令人猝不及防。此次黑死病在1331年首先见载于中国。它由沿丝绸之路旅行的商人们携带,于1347年秋天到达克里米亚。在这里,感染者登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船只。再从君士坦丁堡开始蔓延到西西里、希腊、埃及、北非、叙利亚和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到1347年底它已经以最危险的肺炎鼠疫形式抵达基督教世界的商业中心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贸易城市。受感染的城市很快就看到尸体堆积如山:死亡率超过40%成为常态。
瘟疫的消息比感染本身传播得更快。收到预警的城镇紧闭城门,禁止旅行者进入。但当不得不偶尔开门运送食物和其他供给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小如跳蚤那样的东西。面对瘟疫,无人幸免: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妇女还是儿童,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信众。在突尼斯,伊本· 赫勒敦写道:“就仿佛世上的生物发出了呼声,请求被遗忘……而世界响应了它的呼唤”。阿尼奥洛· 迪图拉描述他在锡耶纳的经历:
死亡始于5月。它残酷而恐怖。对它的种种残忍和无情,我不知道从何处说起……父亲弃子归西,丈夫没了妻子,兄弟接连死去。因为好像只要人一张嘴呼吸,一睁眼看东西,疾病就会来临。家人至多只能把死去的亲人拉到沟里,没有牧师,没有祈祷……而我亲手掩埋了我的五个孩子……那么多人死去,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
佛罗伦萨是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大约有60%的人口死亡。一个亲历者报告说:
人们除了把尸体运出去掩埋,其他事情便无能为力了;许多人死前都来不及忏悔,或接受最后的祈祷;许多人孤独地死去,许多人死于饥饿。每个教堂都挖了深及地下水位的大坑,那些夜间死去的穷人被迅速收集起来,扔到坑里。早上当人们看到坑里已积有大量尸体时,就覆盖些泥土在上面;随后又有尸体堆放其上,人们再覆盖一层泥土,就像烤意大利宽面,铺一层通心粉,再加一层奶酪。
诗人薄伽丘看到生者如何处理死者时,深受触动。他写道:“害怕被腐尸传染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死者的慈悲,邻里们常见的做法就是用双手把尸体从房间里拖出来,放在门前,每个出来走动的人都能看见这些尸体。”而佛罗伦萨作家乔凡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自己也成了这场瘟疫的受害者。他笔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瘟疫一直持续到……”还来不及填上日期,瘟疫就用黑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1348年1月,瘟疫已经抵达法国港口马赛。然后从那里北上穿过法国,向西进入西班牙。它的致命危害并没有减弱。在佩皮尼昂(Perpignan),125个公证员中有80个死亡,18个医疗理发匠有16个死去,9个内科医生死了8个。城镇繁荣的信贷业务则完全停止。在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自从克莱门特五世1309年移驾于此后,教皇们就一直驻跸在这里,有三分之一的红衣主教染疾去世。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有一半的人死亡。而疾疫仍在蔓延,向四面八方传播。勃艮第地区的日夫里(Givry)是个自1334年起就有教区记录的村庄,它见证了该村掩埋人数由年均23人,增加至四个月内就有626人下葬,这意味着死亡率达到50%左右。在英格兰,每个教区都有超过40%的牧师死去:埃克塞特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神职人员。在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农村地区,农民平均死亡率为42%,但这个苍白的数据覆盖了不同地区,从幸运点的哈特尔伯里(Hartlebury,19%),到疫情严重的阿斯顿庄园(Aston,80%)。英格兰的两个最大的城市,伦敦和诺威奇,死亡率都达40%。1349年7月初,有一艘来自伦敦的商船在挪威的卑尔根(Bergen)港口附近飘浮。当地负责人登船查看时,发现船员已经悉数死去。他们惊恐万分,赶紧下船回到岸边。但是太迟了:其中一人已经染上时疫,黑死病就这样来到了挪威。
有多少人死于黑死病?罗马教廷官员计算出的数字是约2400万基督徒,占基督教世界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死亡人数很可能更多:法国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约达60%;英格兰、加泰罗尼亚和纳瓦拉地区可能略高于60%;意大利在50%—60%之间。显然,如此规模的死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因为那些处理基本日常事务的牧师、仆人、厨师、放牧者、收割工人和幼童的母亲完全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1340年,像1316—1319年饥荒年月那样高的死亡率已经超出想象了,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有比那时更糟的情况了。然而从1347年开始,欧洲人不得不为死亡做好一切准备。事实上,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做好准备,因为这一年的黑死病只是流行疾疫袭击的第一波:它于1361—1362年、1369年和1374—1375年死灰复燃,并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平均每隔8—12年复发一次。尽管以后的爆发都不如第一次严重,但仍然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例如1361—1362年的瘟疫爆发一年内就抹去了英格兰10%的人口。一个世纪后,1478—1480年的大爆发同样夺去了10%—15%的人口的生命。即使黑死病过去300年后,瘟疫的爆发依然能夺走一个中等规模城镇15%的居民的生命。大城市情况则更为严重。1563年伦敦超过20%的人口死去,1576年的威尼斯、1649年的塞维利亚、1656年的那不勒斯、1720—1721年的马赛,死亡比例甚至更高。14世纪昭示着一个恐惧的时代。人们意识到每天晚上上床睡觉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夜晚。
然而,在这本书的语境里,瘟疫的致命性不是其最重要的特征。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社会并没有崩溃。人口死亡过半并不意味着人们抛弃了财产所有权规则,或放弃了播种和收获的循环。一些地方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是暂时的。在佛罗伦萨,掘墓人洗劫弃宅,勒索不敢离开家园的受害者,欺凌无助妇女,但这类不法行为只持续了数周。尽管许多高级教士和权贵死于瘟疫,但很快有人接任。欧洲的统治者表现得也很勇敢。在英格兰,爱德华三世公开宣布,他将前往法国,而那里此时瘟疫肆虐。他确实去了,虽然只是很短一段时间。他还于1349年4月在温莎举办了一场参与者众多的骑士比武大会,并在期间成立了嘉德骑士团(Order of Garter),即使英格兰本身深受瘟疫之苦。他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他相信上帝对他的佑护。此外,他坚定地向臣民们展示,他相信自己受到上帝的认可。这是一种勇敢的姿态,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女儿已经罹难。
无论是从世俗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黑死病的长远影响。中世纪社会曾一度非常刻板,人们听任上帝分配他们以不同的位置。庄园主就是天生的武士,披坚执锐、领兵打仗。鞋匠就是鞋匠,其他什么也不是。耕种庄园主八英亩土地的非自由隶农就只是个隶农,仅此而已。这些角色是上帝的决定。现在人口急剧下降给这个僵化的结构带来了巨大的裂缝。最重要的是劳动力严重短缺。失去家庭的工人们不再接受被奴役的生活方式: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他们可以随便到最近的城镇出卖劳动力。对于家有挨饿的孩子的农民,如果邻近地主能提供更好的工价,他们就不再满足于为他们的主人耕种几片土地。如果主人想留下他继续服务,就得支付更高的工价或奖励他们更多的土地。
没有什么能像黑死病那样清楚地将中世纪分成早期和晚期。尽管本章一开始提到的饥馑暗示着13世纪的乐观主义在1347年之前已经荡然无存,但瘟疫彻底撼动了每个人对其在世间位置的理解。有些人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聚落中的人几乎全部死光的事实,他们当然也会质问上帝为何如此不公,尤其是看到邻近村庄疫死人数较少的时候。能否认为上帝用这种令人痛苦和畏惧的疾病杀死摇篮中的婴儿是为人类谋求福祉?瘟疫对人类社会的毁灭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瘟疫发生?很多人开始反思卜尼法斯八世(Bonifare Ⅷ,1294—1303 年在位)继位以来教皇的堕落。从他掌教开始,教会高层越来越唯利是图,牟取暴利。教皇们在法国国王的影响下不断堕落,他们在基督教世界的眼里已经蜕变为世俗国王苍白的影子。人们开始怀疑罗马教会是否引领他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走。也有人怀疑瘟疫是上帝因宗教领袖的堕落而对整个人类的惩罚。
瘟疫也改变了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你可能以为死亡是人类生命中极少的必然环节之一,但事实上它极易变化。死亡本身并不存在,它没有实物,因此它只在生者心中有意义:当生命缺席和当人们相信死后有某种不同的生命形式时。后者是变化发生的地方。14世纪整个欧洲都与死亡结下了缘:文学中充满了魔鬼、炼狱和死后生活的色调;在宗教绘画和雕像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骷髅头这个意象。在英格兰,罗拉德派(Lollards)教徒提倡更有激情、更精神化的生活。该世纪末的罗拉德派骑士和高级教士的遗嘱越来越强调立遗嘱者肉身的可憎和罪衍。骷髅(Mementi mori)——我们所有人总有一天会变成的尸体之残骸——被刻在石头上,竖立在大小教堂之中。越来越多人赞助建立礼拜堂和虔诚的基础—建设桥梁、学校、济贫院和为旅行者服务的医院。在这些虔敬行为和对自我憎恨的举动下面,我们能觉察到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人类在上帝眼中的地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是上帝决定把人类整个抹掉怎么办?1348年之后,人类的灭亡看来存在着现实可能性。
然而,对某些幸存者来说,黑死病打开了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的大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受惠者包括那些农民,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出售劳力,赚取比以前在领地耕种更多的钱。英格兰和法国都出台过规定限制自由市场垄断工价,但收效甚微。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对主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可以坚持要求得到更有尊严的对待。如果受不到足够的尊重,他们就可以反抗。以前农民没有反抗的意愿,但是一场瘟疫使他们获得了自我价值感。这引发了许多起义,比如巴黎的扎克雷起义(135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1378年)和英格兰的农民起义(1381年)。的确,我们在历史中很容易注意到,大量的死亡突出了男女劳力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他们自己还是在统治者眼中。
一些与瘟疫毫不相关的社会领域也受到深刻的影响。婚姻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332年,生活在多康比庄园的女奴斯莫尔里奇(Smallridge)的艾格尼丝,想要嫁给莫顿的一个自由人、剪羊毛的罗杰。这个请求被送到坎特伯雷的修道院副院长,即多康比领地的领主那里。副院长拒绝了,因为此次婚姻将使艾格尼丝获得自由。虽然1332 年农奴制依然可以主宰人们的生活和幸福,但到了1400年,这个体制却几乎在西欧的所有地方都分崩离析了。1374—1375年第四次瘟疫流行之后,农民要付的地租下降了,因为佃户减少了,土地却很多。有些借贷过重的领主突然发现自己债台高筑,于是被迫把整个领地租赁或卖给城里的企业家。像斯莫尔里奇的艾格尼丝那样的女人,只要付给领主一点罚金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她们的意中人了。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约束被金钱关系所取代。金钱取代了强制的忠诚。资本主义在城市取得胜利以后,又开始在农村取代封建主义。
我们在这里只粗浅地涉及黑死病带来的一些主要变化。尽管如此,如果基于此书的目的来评估这一时期,那么1347—1352年可能是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期。唯一能与其相比的可能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岁月,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都经历了迅速的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时代:那时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突然莫名其妙地痛苦死去,那么,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也会黯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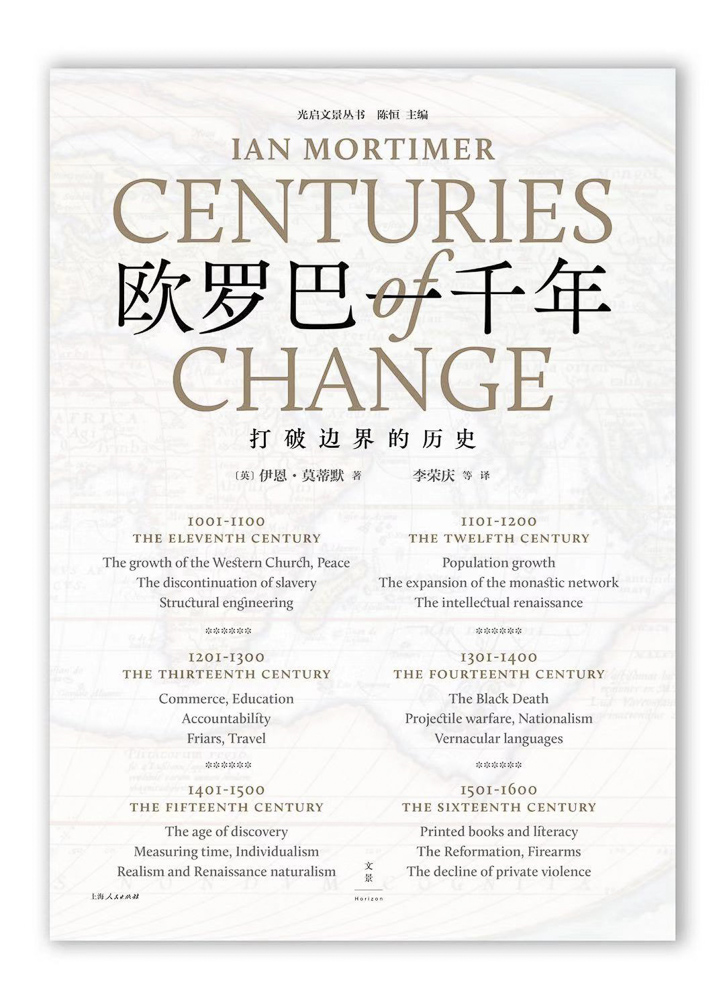
《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 完——
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 1967— ),英国历史学家、作家。1998年入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资深会员;2004年论文《医生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Doctors)获皇家历史学会亚历山大奖。著有《漫游中世纪的英格兰》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