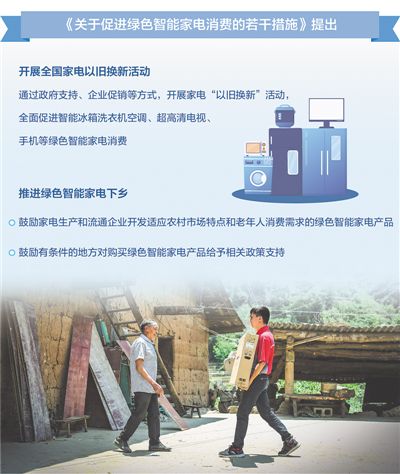君不见,西游文化从不过时,在每个年代都可以凭借其独特魅力融入时代:央视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连年位居各视频网站播放量前列;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电影《大话西游》、网络文学《悟空传》,以及各种戏谑的“西游”作品,乃至“西游”表情包,都是这部传统文学经典与时代、与社会、与各种艺术样式发生的精神共振。
与“四大名着”或“四大奇书”中的其他三部相比,《西游记》具有独特的魅力。从读者面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具有金戈铁马的阳刚风格,一些女性读者似有本能的疏远,《红楼梦》则有不同程度的“少儿不宜”,唯独《西游记》能与大众产生全方位的共鸣。无论男女老少、黄发垂髫,都可以津津有味地与人说起《西游记》的故事。
《西游记》的独特魅力、它的艺术经典性是如何炼成的?《西游记》不是“天降”奇书——它有来历可寻。
其一,文学源于生活,经典来自现实,《西游记》的经典性源自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壮举。关于玄奘取经的史实,各类史书记载略有差异,可大致梳理为:
贞观三年(629),玄奘从首都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偷渡玉门关,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出热海(凌山大清池,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携带657部佛经和大量佛像,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尼泊尔,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丝路南线回国,逗留于阗(今新疆和田市)两年后,回到长安。
行程5万里,途经百余国,历时17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中国故事”。在那个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导航、没有翻译软件的时代,玄奘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难完成的任务。在西域的17年里,他“见不见迹,闻未闻经”——见到了许多以前不曾见过的异域风土人情,也听到了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佛教理论。
《西游记》是神话化的“西游故事”。史书所记“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被形象化为“九九八十一难”,“苦历千山,询经万水”的艰难旅程,化为笔底烟霞。古人评论《西游记》“奇地、奇人、奇事、奇想、奇文,五奇具备”,揭示了《西游记》宝贵的审美精神与艺术风格,也体现出这一“中国故事”独特的叙事方式。
其二,《西游记》的经典性来自时间的赐予,这部作品经历了长达千年的经典化历程。
早在唐初玄奘在世前后,西游故事便有所流传。取经归国后,玄奘奉敕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了西域地理、历史、道里、风俗。他的弟子慧立、彦悰为了表彰恩师的丰功伟绩,谱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一记一传”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传主行迹神奇,书者文采斐然,共同开启了“西游故事”的文学性书写。它们理所当然成了《西游记》的最早源头,也成为《西游记》经典化的开端。
沿着时光长河缓缓流动,晚唐五代到宋元之际,出现了各种体裁的西游文艺作品。开始时,大家各显神通,各有讲法,严肃的历史真实、浪漫的文学想象和活泼的民间传奇,融汇交织。慢慢地,人物和故事逐渐趋于一致,出现了集大成者《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
此后,民间艺人再讲说西游故事时,大致都按这个话本底稿来讲说。现存《诗话》的产生时代已不可考,有人说是宋,有人说是元,也有人认为晚唐五代即已出现这部作品。但可以确定的是,《诗话》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游题材的文学文本。胡适视其为《西游记》的“祖宗”,鲁迅称其为《西游记》的“先声”。
《诗话》对《西游记》最终成为经典性神话小说具有奠基性、先导性的意义。比如,正是在《诗话》中,猴行者首次加入取经行列,替代玄奘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这个猴行者来头可不小,他来源于民间西王母神话,人、神、猴三位一体,是“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他身世奇特,神通广大,“九度见黄河清”,因偷吃王母的蟠桃被发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这显然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紫云洞则在《西游记》升级为水帘洞。
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直接影响了《西游记》的内容和结构。猴行者的出现,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他亦人亦猴,亦仙亦妖,能腾云驾雾,变化作法,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阻碍,必须引入妖魔鬼怪,才能显其神通;随着妖魔鬼怪的出现,唐僧的保护者也须相应升级,于是引入了西天诸神;一般的得道高僧只是精通佛理,既不能长生,又无诸般神功,在猴行者与神魔面前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端坐云中、若即若离、至高无上的佛祖,而非历史上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胜任。就这样,神、佛、魔三者齐集,从此,西游故事的内容和结构驶入了神话小说的轨道。
《诗话》还开启了西游的降妖模式,将玄奘取经的历程浓缩为更具象征意义的“九九八十一难”。据考证,现存《诗话》中的降妖历难故事,完整的有树人国遇妖术、火类坳遇白虎精、九龙池遇九头鼍龙等“三难”。“三难”虽少,但意义重大:它将历史上玄奘所经历的“百千无以备叙”的“此等危难”,演化成为生动形象的神魔故事,为后世《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
到了明代,西游故事更加发达、丰富,逐步形成了戏曲与平话(民间说书话本)两个系列,现存的代表作分别为《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这两部作品是明代《西游记》演化的“关键少数”。从时代考量,它们离《西游记》最近,又同属于叙事文学体裁,适合讲述,共同构成了《西游记》的直接蓝本。
《西游记杂剧》,明初戏剧家杨景贤着,全方位叙述了唐僧取经故事,具有六本二十四则的宏大规模,比王实甫“天下夺魁”的《西厢记》还多出一本,可谓元明以来杂剧之冠。《西游记平话》,明代无名氏着,全本已佚,目前仅存一些片段,主要是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所录“魏徵梦斩泾河龙”和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载“车迟国斗圣”两则。后者还有9条注释,涉及的西游降妖故事十分丰富。
《诗话》尚无猪八戒和白龙马的影子,沙僧的情形则更类似于其他除怪故事:他化为金桥帮助唐僧渡过深沙河,但并没有成为唐僧的徒弟参与取经。但在《西游记杂剧》与《西游记平话》中,“取经班子”的构成及其分工则已经定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是主角,沙和尚、白龙马是配角。
在后世百回本小说成书过程中,人物越来越庞杂,但“取经五人组”的班子始终相对稳定:师徒四人,外加白马,定格为《西游记》的“标配”,其余人物皆跑龙套,穿场而过。
同时,《西游记》的情节构架也宣告固化,为大众所熟知、独立成篇的《西游记》“三大板块”就此定型。这“三大板块”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记、唐太宗入冥记(取经缘起)和唐僧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
其三,《西游记》的经典性,还来自天才作家吴承恩的生花妙笔。
当下学界对“吴承恩着《西游记》”的说法还存有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西游记》的作者是客观存在的。据鲁迅、胡适的考证,最后创编并推出《西游记》百回本巨着的,是明代作家吴承恩。所以,我们不妨将“吴承恩”当作《西游记》作者的一个指代,用以考察这位天才作家的卓越创造。
与《红楼梦》等文人案头文学相比,《西游记》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小说。千百年来,街头坊间的口耳相传,戏班乐坊的浅吟低唱,早已让西游故事初具规模。玉在石中,只待巧手打磨。
吴承恩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独立创作型作家,而是像冯梦龙、余象斗一类的改创型作家。在对以往西游故事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加工和润色的过程中,吴承恩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彰显。
比如,孙悟空与二郎神的斗法故事,在前代杨致和简本《西游记传》中不足300字,而他却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言,使故事更加饱满生动,文字更加神骏丰腴;白骨精的故事,虽在前代《诗话》里早有雏形,但白骨精善于伪饰变化、千方百计“吃唐僧肉”的情节,则完全是吴承恩的构思。
此外,从理论上说,凡是前代西游作品中没有出现和提及的故事,如通天河唐僧坠水、荆棘岭三藏谈诗等故事,都是吴承恩独立创作的精彩篇章。
更值得后世称道的是,正是吴承恩,才将《西游记》写成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神话小说。按以往文学史的命名规则,表现“西天取经”母题的西游“记”,大概率应该像《马可·波罗游记》或《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或者,从“取经求法”的题材上看,它更有理由成为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然而,《西游记》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最后以神话小说定型,是历史选择、创造的结果,更是吴承恩选择、创造的结果。